(2011/09/02)
凌晨五時抵達Samarkand,此時公車和mini bus都尚未營運,所以我一下火車,馬上尾隨一位西方面孔的人,估量是否有shared taxi的機會。幸運地,這位英文不甚好的西方人願意與我共乘到旅館,然後他再轉乘至帖木兒的原鄉Shakhrisabz。我選擇到廉價背包客旅館著稱的Bahodir B&B,一間兩張單人床,殺價至10美元成交後,關上房門,雖然環境不甚佳,我依然累得倒頭就睡。
直至聽到樓下傳來陣陣用餐聲響,我起身梳洗後,下樓用餐。長條桌已坐有數位西方遊客,我與一位法國女子比鄰而席,她懷中還抱著三歲的可愛小男孩。她在言談間透露,她帶著小男孩四處自助旅行,甚至到過非洲。一個人到陌生的異地旅行,本就會遇到奔波、生病等之累,對自己身心的調整都需費一番功夫,何況她還帶著一名小小孩?況且,這個法國小男孩已經在烏茲別克生病:發燒和腸胃炎。我只能說這是一個比單身女子背包客更勇於冒險的母親。
我不知她這樣攜子遊歷的舉動是不是典型的法國人,不過我能確定她對我的反應是典型法國人模樣。一聽聞我從台灣來,第一個話題就是-蔡明亮,她是蔡明亮的粉絲,每一部電影都看過,甚至怨嘆大部分的台灣人沒看過蔡明亮的電影。
她問:「蔡明亮的電影是在描述台灣人嗎?」
我實在沒有辦法班門弄斧,雖看過幾部蔡的電影,但不至於部部必追著看,但我相信蔡明亮描寫的內心世界,絕對不只是適用於台灣人。
我回答:「他應該不只針對台灣人的情況,而是描繪所有人在孤離的狀態。」
法國女子滿意地點點頭,又開啟另外一個話題:台灣人吃魚翅。她批評台灣人殺鯨魚,她的說法是鯨魚是繼恐龍之後,最古老、聰明的哺乳類。我內心咕噥:哎喲!假如我有能力吃魚翅,我現在就是住星級大飯店,而不會住在這廉價背包客旅館了!
出國後,台灣在國際嶄露頭角的大小事,成為外國人認識我的一種途徑。若是好事,可能是禮貌的外國人唯一與我聊天的話題,主要是他們也想不出什麼可聊,不過這種話題大多侷限於台灣電影。若是壞事:政治上的兩岸關係、社會上失業父母攜子自殺,現在連殺鯨魚都成為我背負的原罪。在Bahodir的早餐,是一連串解釋「何謂台灣」的討論,也許這是我選擇住在Hostel的原因,遇見不同的人、獲些旅遊資訊、聽聽有趣的想法,這遠比窩在飯店自己的房間,只瀏覽觀光名勝,卻無法交流來得有趣。
Samarkand是一座大城市,矗立著幾座舉世聞名的古蹟。首先,我步行至最為人知曉宏偉的Registan。可惜因為之前音樂祭的舞台布幕尚未拆除,無法取得宏觀的取景。今早一同share taxi的西方人就跟我抱怨,他前幾天待在Samarkand時,正逢音樂祭,但這些表演似乎沒有開放給一般民眾,他不得其門而入。我在Khiva遇到擔任文化組織理事長的台灣人不就是受邀參加音樂祭嗎?看來此處的音樂表演是分等級,可上達天聽,卻無法下至民眾。
再走到帖木兒的陵寢Gur-E-Amir Mausoleum,傳奇人物總有些傳奇故事增添其丰采,此陵寢讓人意想不到的樸素,其實原本帖木兒已在他的家鄉Shakhrisabz興建自己的陵寢,在Samarkand的陵寢則是留予他的孫子繼承人。但是當帖木兒在前往中國征討的過程中,於哈薩克意外身亡,遺體又因大雪阻塞,無法運回家鄉安葬,最後就落腳於現今Samarkand的陵寢。
欲前往Bibi-Khanym Mosque,但方向感不佳的我,反而闖進Old Jewish Quarter,這裡的小孩不像Khiva的小孩一樣,不斷要糖果和筆,或搶著拿我的照相機,這裡的小孩頂多說一句こんにちは(日安),不過倒是一樣很愛被拍照,他們奔跑、嬉鬧、提水、玩水,雖知道我是闖入者,但依然以平常心自在行。


我尾隨一位提著購物袋的人而行,也順利找到Jewisher Quarter的出口,先到Siob Bazaar,小販極力的招呼吆喝我試吃,不過總覺得他們開價過高,往往都要砍價,可是我又摸不著實際的物價,買東西也是挺辛苦的差事。
 Siob Bazaar旁即是Bibi-Khanym Mosque,Bibi-Khanym Mosque的故事性遠大於其建築的可觀,Bibi-Khanym Mosque中間有一拱型大理石,據傳如果女性爬行通過,將會多子多孫。Bibi-Khanym是帖木兒的中國妻子,趁帖木兒遠征時,想要興建這座mosque給帖木兒一個驚喜,沒想到建築師瘋狂愛上Bibi-Khanym,威脅Bibi-Khanym允許他一吻,否則不願完工,想當然耳帖木兒撞見這一幕,不但處死建築師,更要求從此女性需穿戴面紗,以免她們的外表會勾引了男性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男性只重視外表,缺乏自制力,又把過錯要女性承擔,是自古到今皆然的道理。
Siob Bazaar旁即是Bibi-Khanym Mosque,Bibi-Khanym Mosque的故事性遠大於其建築的可觀,Bibi-Khanym Mosque中間有一拱型大理石,據傳如果女性爬行通過,將會多子多孫。Bibi-Khanym是帖木兒的中國妻子,趁帖木兒遠征時,想要興建這座mosque給帖木兒一個驚喜,沒想到建築師瘋狂愛上Bibi-Khanym,威脅Bibi-Khanym允許他一吻,否則不願完工,想當然耳帖木兒撞見這一幕,不但處死建築師,更要求從此女性需穿戴面紗,以免她們的外表會勾引了男性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男性只重視外表,缺乏自制力,又把過錯要女性承擔,是自古到今皆然的道理。
微爬小坡,走到Shah-I-Zinda,付了門票+照相費共8,600sum,只見隔壁的烏茲別克人用驚訝的表情看著我支付的價錢,旁人跟他解釋我是外國人,當地民眾只要付幾百sum。Shah-I-Zinda是帖木兒家族或伊斯蘭先知的陵寢,鄰坡而築,層層伊斯蘭建築比鄰而立,花纹裝飾各有不同。遇到一對可愛中年夫婦來自烏茲別克東部費干納地區的Kokand,他們不斷好奇詢問我問題:結婚沒?飛機機票多少錢?臺灣首都在哪裡?結果那位先生一直叫我Taipei,直到他太太問我的名字以前,他才拗口的念我麼名字。他們付費請人拍照留念,還邀請我一同的加入,我不斷推辭,畢竟這應該是他們難得的合照,不過,他們極為堅持,也許對於他們而言,我也是有趣的風景之一吧!Shah-I-Zinda後方是穆斯林墓園,英國情侶Richard和Sian後來跟我說,他們本是在墓園研究穆斯林的墓碑,走一走就進入Shah-I-Zinda,沒有付任何門票。
跟來自Kokand的夫婦揮揮手道別,決定折返用餐。旅行至今已經第九天,難得的順利,沒有火車停駛、沒有掉行李、沒有被性騷擾,更沒有腸胃作怪,真是太難得了!思及至此,我不免興高采烈的想要慶祝一番,我選定Registan對面的餐廳,點了冰涼的啤酒,在二樓坐位眺望Regitan的景觀,好不盡興呀!也許是太久沒有喝酒,也許是潛意識在伊斯蘭國家飲酒是種冒犯,也許是老天不會讓人生旅途太順遂,甫下樓梯,離開餐廳,我馬上覺得dizzy,臉色紅通通,在街上腳步踉蹌,舉步維艱,身體左傾右歪,沒想到又偶遇Kokand夫婦,我也只能癡癡地傻笑打招呼,勉牆舉步回到旅館,借用電腦一會兒,覺得異常不舒服,一鼓悶暈昏眩感,我趕緊衝回房間,人還沒到門口,就作嘔,掩口衝進廁所,嘔吐物一瀉而下,緊接著肚子咕咕作響,狂拉肚子。畢後,我虛脫無力地躺在床上,不斷大量冒汗……
一小時過後,體力稍稍恢復,用僅存的力氣下樓,旅館的職員得知,告知我可能是食物導致輕微中毒現象,他說在烏茲別克有食物中毒情況大多是白種人,我是他第一個遇到的Chinese有此狀況的人。我真是哭笑不得,沒想到我自恃與白種人柔弱的腸胃不同,最後卻在烏茲別克的眼中,不過是同類品種。
幸好這次症狀算輕微,還有力氣記下當日的日誌,書寫一半,聽到外頭有敲敲打打聲音,至外頭瞧瞧,原來是一場將女方迎娶至男方的婚禮儀式,他們興奮的昭告天下,我獨自駐足旁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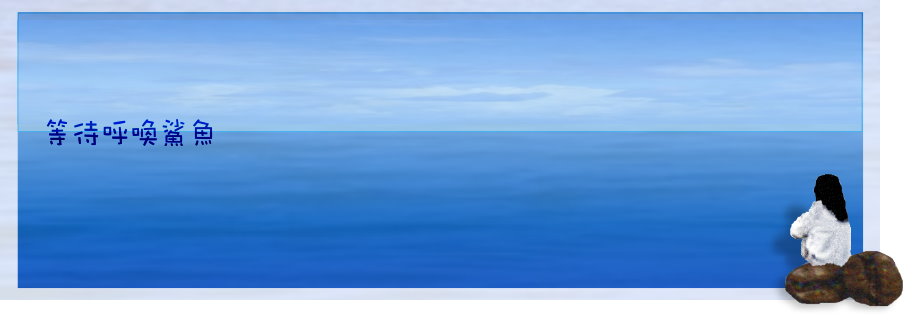







0 comments:
張貼留言